关于书
今天见了蛮多人在说着世界读书日这事,说实话,我还是头次知道这个日子,然后又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是几号,懒得去确认。
阅读,还是不阅读,跟今天是不是读书日有什么关系么?
我爱不爱你,跟今天是不是你生日有关系么?
当然,这得先找个人爱了,所以,这又是一个伪命题。
扯远,本想认真写篇东西推荐几本书,推的每本书都会有故事和回忆,便会有了灵魂血肉和美好,但是呢,好像一直遥遥无期的感觉,时间不够,杂务太多,进入不了这个状态。却有巧了今这么个日子,一时兴之所至,随意唠叨几句。
《依靠自我》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,高中时期阅读,它教会我不盲从,不从众,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,哪怕在外人眼中有时候只是固执。很薄的一本小册子,源于美国,爱默生。
王小波的所有书籍,尤其是后期的杂文,还有他给李银河写的情书。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也是高中时候所看,那时候对老三届、对知青下乡又了另一个活络的真实的感受。而这些个在其他作家诸如贾平凹、赵树理等等之中所感受不到的。王小波杂文、《黑铁时代》里的中短篇传奇式小说推起。大器晚成之人,翻来覆去多次而不厌烦。
余杰的早期,从《冰与火》到《香草山》到《铁磨铁》之中的些许,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,你会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与平时的主旋律和表面太多不符不同的东西,赤裸而直接。有点类似于年轻时候的李敖。
李敖曾经是我很喜欢的作家,尤其是早期的作品,受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的影响,对谭嗣同的感官和了解远远大于梁任公和康有为等人,高考作文里竟然用了这个人物模型,然后就是估摸着跑题了,虽然如此,我也没有记恨李敖,我太他妈的大肚了,就像我在作文里填了首小令,那是因为早期对此有着分外的欢喜。
小令是我最喜欢的古体,这里指的是宋词中五十八字以内的词牌,如梦令、长相思、江南子等等,元曲的小令不熟悉,也不算。我记得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的前几年,无论是上课、放假、游玩,随身都会携带几本书,其中有一本必然是《唐宋小令三百首》,常因为突如而至的几个字几句话而将情入绪几小时,然后再把词谱翻出对着平仄,成时心满意足甚而自得,虽然这些个东西在现在自己看来大多烂到了姥姥家。
说到了小令便必然会说到诗歌,早期接受的诗歌映像深的好像是海子的诗集,噢,对了,是汪国真的,那个在90年代嚷着要评诺贝尔的诗歌量产式“大师”,真想说个我去,这样子也可以。海子的诗,是我读过的国内现代诗歌里面最好的,这里的最好指的是单篇的质量,也是整体的质量,那种直指人心刺痛人心的句子,不煽动,不乱情,远超他人。后来,陆陆续续看了顾城、北岛等等,不算大欢喜。倒是国外的有几个大爱,翻译很重要,查良铮老师,或说穆旦老师翻译的雪莱的诗歌、杨武能老师翻译的海涅的诗歌等等。早时候背过很多,小令,唐诗,古文,还有现代诗歌,在长途车上,在角落发呆,在晨起而不能回,现如今早都忘,那份美好却记得,还有那份韵律。
既然说到了译作,就不得不提下《莎士比亚悲喜剧集》,于个人而言,朱生豪先生版本胜了梁实秋先生。至于王道乾老师的《情人》韵律是真好,只是不知为何,寥寥看几眼总不能续久,有点愧疚。那时候有个说法,最好的作家都去翻译国外的作品,时代所然。
再然后,说到看书不能续久,原因可能是不对胃口和喜好,但总觉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,还是在于韵律。我看老子孟子庄子之类,也看不长久,但好歹还过了遍,可尼采之类真心抗不下,初始以为哲学太哲学,根本就不是一路人,直到看了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略》,大为改观。有些书是要作为专业书的,我们大可不鸟,但还是更期望能有更多的更接人气的更让人舒服的文字,让我能念之,欢喜之,而爱之。
还有很多,还有太多,不展开,本是随意而絮叨,焉能事事而周全。
有所读,有所思,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这便是阅读的意义。
阅读,还是不阅读,跟今天是不是读书日有什么关系么?
我爱不爱你,跟今天是不是你生日有关系么?
当然,这得先找个人爱了,所以,这又是一个伪命题。
扯远,本想认真写篇东西推荐几本书,推的每本书都会有故事和回忆,便会有了灵魂血肉和美好,但是呢,好像一直遥遥无期的感觉,时间不够,杂务太多,进入不了这个状态。却有巧了今这么个日子,一时兴之所至,随意唠叨几句。
《依靠自我》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,高中时期阅读,它教会我不盲从,不从众,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,哪怕在外人眼中有时候只是固执。很薄的一本小册子,源于美国,爱默生。
王小波的所有书籍,尤其是后期的杂文,还有他给李银河写的情书。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也是高中时候所看,那时候对老三届、对知青下乡又了另一个活络的真实的感受。而这些个在其他作家诸如贾平凹、赵树理等等之中所感受不到的。王小波杂文、《黑铁时代》里的中短篇传奇式小说推起。大器晚成之人,翻来覆去多次而不厌烦。
余杰的早期,从《冰与火》到《香草山》到《铁磨铁》之中的些许,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,你会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与平时的主旋律和表面太多不符不同的东西,赤裸而直接。有点类似于年轻时候的李敖。
李敖曾经是我很喜欢的作家,尤其是早期的作品,受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的影响,对谭嗣同的感官和了解远远大于梁任公和康有为等人,高考作文里竟然用了这个人物模型,然后就是估摸着跑题了,虽然如此,我也没有记恨李敖,我太他妈的大肚了,就像我在作文里填了首小令,那是因为早期对此有着分外的欢喜。
小令是我最喜欢的古体,这里指的是宋词中五十八字以内的词牌,如梦令、长相思、江南子等等,元曲的小令不熟悉,也不算。我记得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的前几年,无论是上课、放假、游玩,随身都会携带几本书,其中有一本必然是《唐宋小令三百首》,常因为突如而至的几个字几句话而将情入绪几小时,然后再把词谱翻出对着平仄,成时心满意足甚而自得,虽然这些个东西在现在自己看来大多烂到了姥姥家。
说到了小令便必然会说到诗歌,早期接受的诗歌映像深的好像是海子的诗集,噢,对了,是汪国真的,那个在90年代嚷着要评诺贝尔的诗歌量产式“大师”,真想说个我去,这样子也可以。海子的诗,是我读过的国内现代诗歌里面最好的,这里的最好指的是单篇的质量,也是整体的质量,那种直指人心刺痛人心的句子,不煽动,不乱情,远超他人。后来,陆陆续续看了顾城、北岛等等,不算大欢喜。倒是国外的有几个大爱,翻译很重要,查良铮老师,或说穆旦老师翻译的雪莱的诗歌、杨武能老师翻译的海涅的诗歌等等。早时候背过很多,小令,唐诗,古文,还有现代诗歌,在长途车上,在角落发呆,在晨起而不能回,现如今早都忘,那份美好却记得,还有那份韵律。
既然说到了译作,就不得不提下《莎士比亚悲喜剧集》,于个人而言,朱生豪先生版本胜了梁实秋先生。至于王道乾老师的《情人》韵律是真好,只是不知为何,寥寥看几眼总不能续久,有点愧疚。那时候有个说法,最好的作家都去翻译国外的作品,时代所然。
再然后,说到看书不能续久,原因可能是不对胃口和喜好,但总觉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,还是在于韵律。我看老子孟子庄子之类,也看不长久,但好歹还过了遍,可尼采之类真心抗不下,初始以为哲学太哲学,根本就不是一路人,直到看了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略》,大为改观。有些书是要作为专业书的,我们大可不鸟,但还是更期望能有更多的更接人气的更让人舒服的文字,让我能念之,欢喜之,而爱之。
还有很多,还有太多,不展开,本是随意而絮叨,焉能事事而周全。
有所读,有所思,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这便是阅读的意义。
茉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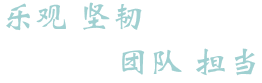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