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百斤的爱
慈孝征文三等奖作品
爱有多重?
我的父亲说:六百斤。
父亲口中所说的六百斤的由来我未曾考证过,但是从我记事起,确实有关于六百斤的一些回忆。
那是金秋十月的乡村,门堂、路边、小学校的操场、畜牧场……处处都是晒谷场,家家户户的筒簟边,放着一箩箩金灿灿的稻谷,丰收的喜悦让人振奋。孩子们在晒谷场里或是嬉戏,或是厥着屁股,拿着簸箕,帮忙将谷子倒满篾箩。在晒谷场的显眼位置,有一杆能称上百斤重的压轴大秤,它是农忙结尾时的主角。
主角登台并不容易,以我们家为例,单薄的三口之家。母亲体质弱,下地吃不消,就在家负责给我们煮煮稀饭。为了把稻子从田地里收割脱粒回来,我家里人得喝上好几天的稀饭,才能完成。
十多岁的我也有幸成为了家里的干活主力。我喜欢在田地里干活。赤着双脚,在软软的泥土里踩出一个个脚印。大人们每行割七八株稻,我就割四株或是三株,捏在我的小手里刚好一把。父亲对我割稻的要求第一是镰刀要放平整,靠近稻根,稻秆就不会被割得一边高一边低,这样在脱粒的时候也不容易戳到脚,二是手握稻秆离镰刀远一些,避免伤到手。割稻的过程基本上是蹲着的,像我们跳蛙步似的前移,我紧随着父亲的步伐,期望自己快点到达对面的田埂,可以得到父亲一个赞许的微笑。一个来回下来,我和父亲的差距就越拉越开了,大腿开始发酸,腰也直不起来,手渐渐没有了力气,镰刀开始在稻秆上机械地摩擦,就好象在锯一棵粗大的木头,怎么也锯不断。父亲看我割不动了,就准备开始脱粒。
我们父女二人得先将一台笨重的半自动脱粒机拉扯到田头,那家伙由一个铁皮槽子、一根木头踩踏板和装在铁皮槽前方的滚轮三部分组成,木头踏板通过齿轮和铁皮槽前的滚轮相连接,踩踏板的人需要步伐一致,才能带动滚轮快速有力地转动。脱粒开始了,我们各自捏着稻丛在脱粒机滚轮上左转右转,铁皮槽里就响起了谷粒儿“嘣嘣”的飞射声。
脱粒有技巧,稻头不能太多放在滚轮上,太多不仅容易把稻叶都脱进去,还会把稻秆都卷进脱粒机里,甚至连人也会拉进去,危险性大。但也不能放太少,因为这样容易脱粒不干净,浪费粮食,在农村,这是极其可耻的行为。
父亲不喜欢脱粒,因为他有腰痛病。腰疼经不起一上一下折腾,所以脱粒的时候就由我负责递稻给他。父亲掌握的脱粒技巧恰倒好处,所以动作很快,一把稻谷在他的手中转几下,就干净了。我不能让他空着手在那里等我,他更不准我慢到让他空踩踏板,白白浪费力气。我从割稻,换成递稻,便精神抖擞,不仅下蹲、起立的动作很轻松,还能奔跑到稍远的地方把稻堆抱过来,一次拿两捧稻,一捧夹在腋下,一捧拿在手上,稻穗对着自己,稻尾对着父亲的斜侧面,这样父亲接手的时候就会更方便一些。少了一次下蹲的时间,我递稻的速度也很快,汗水从我的脸颊上滴落下来,汗水也湿透了父亲的脊背,那时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在脱完粒的稻草堆上坐一下,甚至可以摊一条麻袋在上面,躺一小会儿,或是去抓一下蚂蚱轻松一下……但是父亲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瓶汽水,用牙齿咬开瓶盖,喝了几口,把大半瓶都给了我。“咕咚咕咚”几口汽水下肚,我便有了劲。铁皮槽里的谷子一下子就满了,谷子装满麻袋,堆上手推车,我也高高地坐在麻袋上,带着一天的劳累,沐着夜色回家。
到家后,父亲匆匆地扒了几口饭,还要筛谷、扇谷,以便第二天早上谷子能运到晒谷场晾晒。经过几个日头的爆晒和每天辛勤的翻晒,某个午后,母亲就顶着严严的烈日,掂起脚跟,用竖起的脚尖稍用点力,去搓碾筒簟里的一小挫稻谷,她们就褪去了那金黄的外衣,露出了白白的身体。谷子已经晒干了。
我被委以重任去喊来爷爷对秤花,六百斤就像一个隆重的仪式,开始在晒谷场里上演。秤钩起蔑箩,扁担穿过秤绳。这些日子被日头晒得黝黑的父亲在扁担的这一头,小心翼翼的母亲在扁担的那一头,爷爷在帮忙打秤陀,我就往篾箩里添倒谷子,直到爷爷不断地叫道:“好、好、好!”我则在父母的示意下,再盛上满满一簸箕的稻谷倒进篾箩。我看见爷爷笑起的皱纹开成了一朵菊花,六百斤稻谷分三次装上爷爷的三轮车,倒入爷爷的谷仓,农忙基本结束。我们所有的辛苦劳作就都有了意义。
种单季稻的南方农村,人均大概有三分三的田地,一亩地在好的年成产量有一千斤左右。每个老人的口粮是每年六百斤。每一百斤稻谷现在市场价格在150元上下浮动 ,六百斤稻谷的价格也就900元,那只不过是个冰冷的数字。在农村,六百斤却是爱的重量,也是孝顺的全部含义。
心脑电科 应美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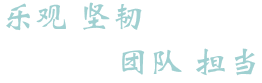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