亮在心头的那盏灯(一等奖)
有一盏灯,它与众不同,就是在白天光线很好的时候也亮着。
第一次见到这盏灯,是2005年冬天一个上午在仙居人民医院的病理科。这盏灯悬挂在一块隔断房间的壁板上,长不过数尺,亮着柔和的白光,这是一盏普通的日光灯,初看并未见到它的独特之处。
在灯的前面,是一台装着恒温水的黑色小盆,上面轮流漂浮过不同病人的石蜡组织切片。我后来才知道,只有借着那盏日光灯照射在水里的反光,才可以看到漂在上面的那些透明的薄如蝉翼的组织。
常有不知情的人,每每发现这盏青天白日都亮着的灯,就会好心地提醒道:“灯是开着的!”不过,我们能听懂言语间认为我们忘记关灯对资源浪费的意思。
病理科的技术员深深地懂得这盏灯鲜为人知的作用。
这盏灯在外人的非议和不解里,无私而执着地亮着,因为它知道自己亮着的意义。这盏灯,是仙医人昼夜“照亮”别人、无私救死扶伤精神的写照。
这盏灯,也照亮着我的从医之路。
记得我工作后第一次挨批评,是因为那瓶放置在花岗岩台面上的液体标本。那日,穿着绿色手术衣的杨含金主任走到了技术室门口,往日那张随和的脸上布满了阴云,他厉声问:“刚才的胸水标本是谁处理的?”我不知所措地点了一下头。他把我带到取材室,指着两瓶胸水又问:“哪一瓶是你处理的?”我目瞪口呆,心中甚是疑惑,因为我刚才做胸水涂片的时候,明明只有一瓶,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两瓶?
杨主任告诉我,当我处理完胸水标本后不久,另一科室的胸水标本也送到了,本来第二瓶胸水上还有一张送检单,但因为窗户开着,风一吹,就掉了。他刚好“见证了”送检单藕断丝连落下的那一幕,才得于杜绝错误的继续发展。
第一次工作的不细致,让我感到极大不安。是的,因为没有把处理过的标本放进医疗垃圾袋,装在两个相同的玻璃瓶内的标本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的。一丁点“疏忽大意”,所带来的后果都不堪设想……
可是,恐慌过后,年轻而又心高气傲的我马上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——没有人曾教我要这样做。我特别不服气,以至于在食堂碰到打饭的杨主任,故意把头转到别处去。
年轻的心特别需要磨砺。后来,杨主任特地给我讲了病理科前辈方复友老师当年如何工作细致、制片质量拿下全省第一的往事,他还交代技术室的同事兼老师:“美萍年轻,一定要严格要求她!”从那以后,技术室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教我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。病理科对每位病人的检查,从收标本到发报告,要经过七遍的三查七对,每日都需要按着号子从ABC开始排列的蜡块和切片曾经让我觉得无趣,琐碎的的流程,一步,一步,居然让我年轻浮躁的心静了下来。不会忘记那台让我抓狂的托盘扭力天枰,它精确度达到0.1mg,即使我轻轻吐出一丝气,都能让好不容易调节好的天平两端摇摆起来,我越急,它越摆,所以我不得不静下心来,让它保持平衡。
若干年后,深入了解了从医的伟大意义,艰苦的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与享受。我们甚至乐此不疲地经常去监测角落里的那瓶蒸馏水的PH值,去扑捉那些酸碱度细微的变化,以适应实验室不同的试剂配置的要求。
今年,是仙医八十周年院庆。我突然想起了那盏在壁板上陪着我亮了六年的灯和病理科的故事,怀念这些年走过的时光。当年的“胸水标本事件”后,我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错误,因为杨主任和技术室的老师们已经用行动告诉我:医者该有的态度与责任,那就是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。老师们明亮的眼睛,和那盏灯多么相似。无论受到怎样的误解、冷眼和诽谤,为医者都要有在风口浪尖上站稳脚跟的坚定与勇气。
感谢病理科的那盏灯,它不光帮我捕捉到了黑色恒温机上那些组织细胞,更在我迷茫的时候照亮了我的心,鼓舞我继续前行。
亮一盏明灯在心头,并且知道它亮着的意义。这或许是仙医八十年一路走来如“卓越者”的语重心长,或许是一个身教重于言教无声指导的好习惯……这,让我在仙医普通的工作岗位上,执着地去追求“工匠精神”。 应美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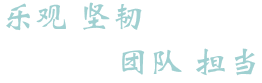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