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的味道
对于在乡村生活过二十余年的我来说,乡村的味道是最熟悉不过的了,这就像蜜蜂熟悉花朵的气息,像鱼儿熟悉水的味道一样。
乡村的味道里,透出勤劳和辛苦。每年春回大地,布谷鸟在不远的山上“布谷、布谷”地催促的时候,农人们一年的繁忙农事就拉开了序幕。这时的水还是比较冰的,但村外的广袤田野里,农民们赶着牛忙碌地翻耕着。翻好后,把发芽的谷种撒进小块农田育秧。之后约莫半个月,秧苗长成,于是插秧又是一项忙碌、劳累又需要及时完成的农活,毕竟农时不等人啊。唐代禅师——契此和尚写道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, 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,我想:农人们不会懂得这诗中揭示的深奥的人生哲理,但是他们踏踏实实、一步一个脚印地栽种生活,栽种人生的精神,让每个人肃然起敬。
风晨雨夕,花开花落,禾苗在阳光的感召下,在雨露的滋润下,一天天地长大,到了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农历六月,金黄的稻浪在田野里翻滚,于是农人一年里最辛苦、最繁忙的夏收夏种来到了。小时候,我曾跟着父母参加过夏收夏种,这份辛劳和忙碌的记忆,深入骨髓,终生难忘。那时候,为了在凉爽的天气里劳动,我们早上三、四点钟就出门了,西斜的那轮明月,撒下如水的清晖,照得田野里的一切清晰可见。我蹲在田头,右手握镰刀,左手抓住一丛稻子,用力割下,放在身后,重复着这个单调而吃力的动作,直到大家齐心协力割完一整亩稻子,这时早已汗湿重衫,几乎能拧出水来了。但是还不能休息,迎着喷薄而出的旭日,父亲和母亲踩着打稻机打稻,我与妹妹递过成束的稻子。在渐渐发出热力的六月的阳光下,我们的汗水就像泉水一般冒出来,连踩过的脚印里,也湿湿的。直到中午十一、二点钟,我们把汗水和着最后一把稻子打进打稻机,才能帮着父母把稻谷用双轮车推回家。
夏日的下午,阳光最为毒辣。这样的时候,自然不能去割稻、打稻,但是也没有机会休息,因为收到家里的稻谷还需要筛谷、扇谷、翻晒等一系列工序,才能归仓。也许只有参加过夏收夏种,才能真正理解唐朝诗人李绅写的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?粒粒皆辛苦。”的含义。
而夏收之后,紧接着的就是夏种,这时往往到了台风影响频繁的农历七月,天上急速飘过的乌云,预示着“山雨预来风满楼”,而决不能耽误的农时,又决定了无论怎样都要把晚稻秧按时插下。于是,我常常跟着父母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,穿着雨衣,在田里插秧,经常泡得手指、脚趾发白,长时间弯腰,弄得腰酸背疼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写了一首《四时田园杂兴》:“昼出耘田夜织麻,乡村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诗中虽然写出了农村农忙时的繁忙景象,却没有写出人们的劳累和辛苦,窃以为美中不足。
农村的味道里,也有悠闲和安谧。当春耕春种、夏收夏种、秋收秋种全忙完,余下的就是农闲时间。这样的日子是惬意的,春日里,阳光慵懒地照着村子,屋角墙边,火红的杏花,粉红的桃花,雪白的梨花,开得热热闹闹,花下,毛茸茸的雏鸡成群结队,跑过来,跑过去,撒着欢儿觅食。谁家的大黑狗卧在门口,对着鸡雏吠叫几声,又懒洋洋地卧倒了。夏天,骄阳似火,在阴凉的弄堂口或绿荫遮天闭日的大樟树下,许多人聚在一起,谈天说地,或是听一个老者说故事,说或听得累了,翻过身去,躺在凉席上,就可以睡一个长长的午觉。人们决不会有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”的闲愁闷气,而只有: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的舒心惬意。当秋风吹过田野,菊黄蟹肥,秋高气爽,天青云淡,南归的大雁,在天空留下一串嘹亮的歌吟,漫漶着“鸟度屏风里”的诗意画意。冬日,村子里显得寂寥萧瑟,而下雪的日子则是另一番景象:鹅毛大雪纷洒而下,四周的村路、民居,白雪皑皑,虽没有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。”的壮观,却也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别致风情。
农村的味道里,更有欢乐和甜蜜。每到春节来临,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。腊月二十、二十一,那是约定俗成的大扫除日,勤快的主妇们把天花板、墙垃旮的蛛网、灰尘清扫得干干净净,每家都是窗明几净、洁净舒适。腊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捣糕、做糍粑,早一天,相邻几家约好把籼米和糯米浸在水里,到了次日傍晚,堂前拉起了电灯,亮如白昼,棒小伙子们脱衣挽袖,侍候在捣臼前,谁家糯米、籼米熟了,就抱来倒进捣臼,于是小伙子们轮流用捣杵使劲舂,直到糯米、籼米变得粘稠如胶,再搬到大砧板上,压成糕或糍粑。那时真是孩子们的狂欢节,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走东家串西家,报告谁家糯米才刚上锅、谁家已经熟了的讯息。腊月二十四、二十五做馒头,主妇们用麦麸发酵,再用发酵水把几十斤面粉揉成面团,等到面团发酵好了,就在锅上放上蒸笼,烧火蒸馒头。我们仙居的习俗,这时要做馒头干和肉包子,所以蒸笼里就有馒头、肉包子、馒头干三类食品。有些心灵手巧的主妇,还会做出鲤鱼、轿子、青蛙一类。记得有一年,母亲给我做了几条鲤鱼,惟妙惟肖,让我一直舍不得吃,竟至长了白毛。腊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是杀猪杀羊的日子,村子里四处可以听到猪、羊的哀鸣。那年月刚够温饱,平日里难见荦腥,每家每户都养猪或养羊,为的就是过年打打牙祭。腊月二十八、二十九做过年的最后的准备工作,杀鸡、宰鹅和抽干塘水捕鱼。主妇们还会做好豆腐、泡泡鲞、糊饼。至此,年货就算是准备齐全了。
大年三十这天上午,再把年货拾掇一下。刚吃过午饭,鸡呀、鸭呀、猪头呀就放进锅里煮起来,夜幕降临时分,村子里弥漫着浓郁的香味,叫人馋涎欲滴。年夜饭上桌了,我们小孩子个个放开肚子大快朵颐,这顿饭吃得大家直喊肚子痛。饭后,大人就给孩子们派压岁钱,视家庭经济状况,几毛、几分地给,能得到一元以上的,孩子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此时,主妇们还会炒花生、瓜子、薯条,或是削上几节甘蔗,以备正月初一大家坐着打牌闲聊时作零食。接下来就是守岁了。要等新年来临打了开门炮才能休息,以喻示明年生活红红火火。但孩子们哪经得起“瞌睡虫”的侵扰,没多久就睡着了,被大人抱上床。但睡着睡着,总会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吵醒,睁开朦胧的睡眼,懵懵懂懂地觉得新年到了,然而不久又沉入了梦乡。
新年初一,大家都穿上新衣服,大人们打牌、闲聊,小孩们则四处玩耍,男孩子把小鞭炮点燃扔到女孩子脚边,女孩子尖叫着捂着耳朵逃开,可不一会儿又踅了回来,大家玩得津津有味。从初二开始,是走亲戚拜年的日子,姥姥家、舅舅家、舅公家,干爹家……那些亲戚多的,再加上交通落后,上八(指正月初八)满了还没有走遍。于是,那浓浓的年味,直到正月十五(俗称小过年)元宵节过后,才渐渐消散。
哦,乡村的味道,让每一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永生难忘。
乡村的味道里,透出勤劳和辛苦。每年春回大地,布谷鸟在不远的山上“布谷、布谷”地催促的时候,农人们一年的繁忙农事就拉开了序幕。这时的水还是比较冰的,但村外的广袤田野里,农民们赶着牛忙碌地翻耕着。翻好后,把发芽的谷种撒进小块农田育秧。之后约莫半个月,秧苗长成,于是插秧又是一项忙碌、劳累又需要及时完成的农活,毕竟农时不等人啊。唐代禅师——契此和尚写道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, 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,我想:农人们不会懂得这诗中揭示的深奥的人生哲理,但是他们踏踏实实、一步一个脚印地栽种生活,栽种人生的精神,让每个人肃然起敬。
风晨雨夕,花开花落,禾苗在阳光的感召下,在雨露的滋润下,一天天地长大,到了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农历六月,金黄的稻浪在田野里翻滚,于是农人一年里最辛苦、最繁忙的夏收夏种来到了。小时候,我曾跟着父母参加过夏收夏种,这份辛劳和忙碌的记忆,深入骨髓,终生难忘。那时候,为了在凉爽的天气里劳动,我们早上三、四点钟就出门了,西斜的那轮明月,撒下如水的清晖,照得田野里的一切清晰可见。我蹲在田头,右手握镰刀,左手抓住一丛稻子,用力割下,放在身后,重复着这个单调而吃力的动作,直到大家齐心协力割完一整亩稻子,这时早已汗湿重衫,几乎能拧出水来了。但是还不能休息,迎着喷薄而出的旭日,父亲和母亲踩着打稻机打稻,我与妹妹递过成束的稻子。在渐渐发出热力的六月的阳光下,我们的汗水就像泉水一般冒出来,连踩过的脚印里,也湿湿的。直到中午十一、二点钟,我们把汗水和着最后一把稻子打进打稻机,才能帮着父母把稻谷用双轮车推回家。
夏日的下午,阳光最为毒辣。这样的时候,自然不能去割稻、打稻,但是也没有机会休息,因为收到家里的稻谷还需要筛谷、扇谷、翻晒等一系列工序,才能归仓。也许只有参加过夏收夏种,才能真正理解唐朝诗人李绅写的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?粒粒皆辛苦。”的含义。
而夏收之后,紧接着的就是夏种,这时往往到了台风影响频繁的农历七月,天上急速飘过的乌云,预示着“山雨预来风满楼”,而决不能耽误的农时,又决定了无论怎样都要把晚稻秧按时插下。于是,我常常跟着父母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,穿着雨衣,在田里插秧,经常泡得手指、脚趾发白,长时间弯腰,弄得腰酸背疼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写了一首《四时田园杂兴》:“昼出耘田夜织麻,乡村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诗中虽然写出了农村农忙时的繁忙景象,却没有写出人们的劳累和辛苦,窃以为美中不足。
农村的味道里,也有悠闲和安谧。当春耕春种、夏收夏种、秋收秋种全忙完,余下的就是农闲时间。这样的日子是惬意的,春日里,阳光慵懒地照着村子,屋角墙边,火红的杏花,粉红的桃花,雪白的梨花,开得热热闹闹,花下,毛茸茸的雏鸡成群结队,跑过来,跑过去,撒着欢儿觅食。谁家的大黑狗卧在门口,对着鸡雏吠叫几声,又懒洋洋地卧倒了。夏天,骄阳似火,在阴凉的弄堂口或绿荫遮天闭日的大樟树下,许多人聚在一起,谈天说地,或是听一个老者说故事,说或听得累了,翻过身去,躺在凉席上,就可以睡一个长长的午觉。人们决不会有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”的闲愁闷气,而只有: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的舒心惬意。当秋风吹过田野,菊黄蟹肥,秋高气爽,天青云淡,南归的大雁,在天空留下一串嘹亮的歌吟,漫漶着“鸟度屏风里”的诗意画意。冬日,村子里显得寂寥萧瑟,而下雪的日子则是另一番景象:鹅毛大雪纷洒而下,四周的村路、民居,白雪皑皑,虽没有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。”的壮观,却也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别致风情。
农村的味道里,更有欢乐和甜蜜。每到春节来临,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。腊月二十、二十一,那是约定俗成的大扫除日,勤快的主妇们把天花板、墙垃旮的蛛网、灰尘清扫得干干净净,每家都是窗明几净、洁净舒适。腊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捣糕、做糍粑,早一天,相邻几家约好把籼米和糯米浸在水里,到了次日傍晚,堂前拉起了电灯,亮如白昼,棒小伙子们脱衣挽袖,侍候在捣臼前,谁家糯米、籼米熟了,就抱来倒进捣臼,于是小伙子们轮流用捣杵使劲舂,直到糯米、籼米变得粘稠如胶,再搬到大砧板上,压成糕或糍粑。那时真是孩子们的狂欢节,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走东家串西家,报告谁家糯米才刚上锅、谁家已经熟了的讯息。腊月二十四、二十五做馒头,主妇们用麦麸发酵,再用发酵水把几十斤面粉揉成面团,等到面团发酵好了,就在锅上放上蒸笼,烧火蒸馒头。我们仙居的习俗,这时要做馒头干和肉包子,所以蒸笼里就有馒头、肉包子、馒头干三类食品。有些心灵手巧的主妇,还会做出鲤鱼、轿子、青蛙一类。记得有一年,母亲给我做了几条鲤鱼,惟妙惟肖,让我一直舍不得吃,竟至长了白毛。腊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是杀猪杀羊的日子,村子里四处可以听到猪、羊的哀鸣。那年月刚够温饱,平日里难见荦腥,每家每户都养猪或养羊,为的就是过年打打牙祭。腊月二十八、二十九做过年的最后的准备工作,杀鸡、宰鹅和抽干塘水捕鱼。主妇们还会做好豆腐、泡泡鲞、糊饼。至此,年货就算是准备齐全了。
大年三十这天上午,再把年货拾掇一下。刚吃过午饭,鸡呀、鸭呀、猪头呀就放进锅里煮起来,夜幕降临时分,村子里弥漫着浓郁的香味,叫人馋涎欲滴。年夜饭上桌了,我们小孩子个个放开肚子大快朵颐,这顿饭吃得大家直喊肚子痛。饭后,大人就给孩子们派压岁钱,视家庭经济状况,几毛、几分地给,能得到一元以上的,孩子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此时,主妇们还会炒花生、瓜子、薯条,或是削上几节甘蔗,以备正月初一大家坐着打牌闲聊时作零食。接下来就是守岁了。要等新年来临打了开门炮才能休息,以喻示明年生活红红火火。但孩子们哪经得起“瞌睡虫”的侵扰,没多久就睡着了,被大人抱上床。但睡着睡着,总会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吵醒,睁开朦胧的睡眼,懵懵懂懂地觉得新年到了,然而不久又沉入了梦乡。
新年初一,大家都穿上新衣服,大人们打牌、闲聊,小孩们则四处玩耍,男孩子把小鞭炮点燃扔到女孩子脚边,女孩子尖叫着捂着耳朵逃开,可不一会儿又踅了回来,大家玩得津津有味。从初二开始,是走亲戚拜年的日子,姥姥家、舅舅家、舅公家,干爹家……那些亲戚多的,再加上交通落后,上八(指正月初八)满了还没有走遍。于是,那浓浓的年味,直到正月十五(俗称小过年)元宵节过后,才渐渐消散。
哦,乡村的味道,让每一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永生难忘。
张熠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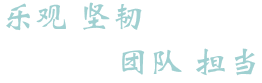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